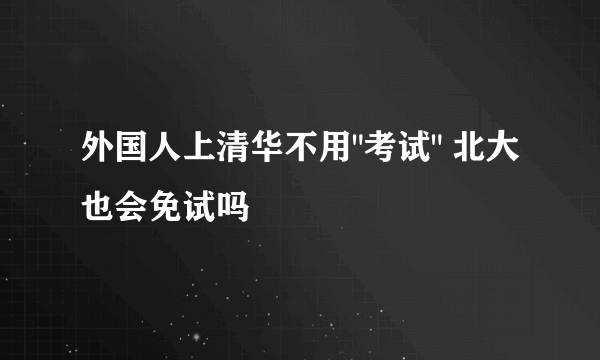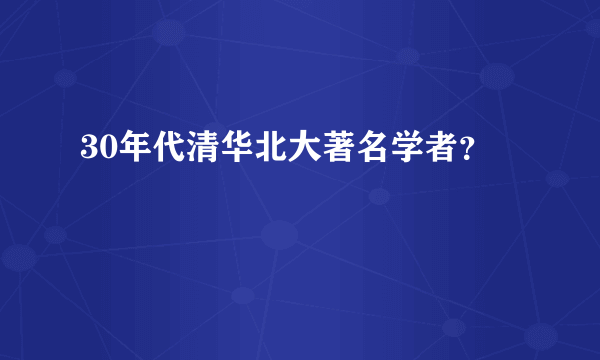清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群殴
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
(▲清华大学学生会抗日救国委员会合影,左一为黄诚。图片来源:清华校友网)
摘要: 梅贻琦治校平衡有度,对左、右两派学生各打五十大板。擅自搜查救国会和学生宿舍、挑起群殴的一批右派学生记过,其中何炳棣“领衔”,因违反校规被记两大过;左派掌控的“救国委员会”予以解散。
“一二·九”运动的骨干很多是高材生。干革命的学生成绩不好,在学校就没有号召力。清华历史系1934级何炳棣是右派学生代表(后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功课极好,颇受教授们器重,但他承认政治活跃的同学中不乏真才实学。
例如和他同级的黄诚,“手笔快,口才好”;吴承明“是清华十级(1934级)头脑最清楚、分析能力最强的级友之一”;姚依林给他的印象最深,“姚的才干和英文令人钦佩”,“他不但在西洋通史第一次月考中成绩优异,并在1934年秋全校举办的英语背诵比赛中荣获第一名。”(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这次西洋史月考,姚依林考91分,何炳棣考89分。姚依林获全校英语背诵比赛第一名时,才是入学不久的大一新生。
清华社会学系1934级学生居浩然(居正之子,孙中山取名)回忆同级同学,也说:“如黄诚、吴承明、姚克广(姚依林)诸拔尖人物,头脑之清楚,反应之敏捷,辞锋之锐利,往往使(高年级)老大哥相形见绌。”(《清华大学十级(1938)毕业50年纪念特刊》,台北1978)
一位美籍华人科学家曾说:“我是‘一二·九’那时候的学生。说老实话我当时在学校只是一个中等的学生,一点也不出色。真正出色的,聪明能干、崭露头角的,是那些当时参加运动投奔了革命的同学。如果他们不干革命而来这里学习,那成就不知要比我这类人高多少倍!”
“一二·九”运动的活跃分子韦君宜,拒绝家庭安排她出国留学,而是继续革命,最终奔向延安,几十年后听到女儿转告的这位科学家心里话,感慨:“他说的全是事实。我们这个革命队伍里有好多当年得奖学金的、受校长赏识的、考第一的,要在科学上有所建树当非难事。但是我们把这一切都抛弃了,义无反顾。把我们的聪明才智全部贡献给了中国共产党的事业。”(韦君宜《思痛录·“抢救失足者”》)
晚年韦君宜以罕见的勇气坦诚反思“我为什么抛弃了学业和舒适的生活来革命呢?”,“是认为这里有真理,有可以救中国的真理!值得为此抛掉个人的一切。”她忏悔自己在政治运动中干的编辑工作,“编造这些谎话,诬陷我的同学、朋友和同志,以帮助作者胡说八道作为我的‘任务’。”(韦君宜《思痛录·编辑的忏悔》)
她也亲身经历“党内斗争很残酷、很坏的一面,其实我们这个党从来就不纯粹”。她这一代奉献自己的鲜血、生命和灵魂,直到“眼泪都已干涸的时候才大彻大悟”,告诉女儿杨团“她参加革命就准备好了牺牲一切,但是没想到要牺牲的还有自己的良心。”(杨团《〈思痛录〉成书始末》)
当然,一个人的精力有限,职业革命必然影响学习。学运骨干曾经成绩优异,不等于一直成绩优异,这是客观事实或者说必然。挂科太多,不仅在同学中没有威信,而且将被学校取消学籍,这是任何一所规范学校的铁律。
于是,有人放弃学业,例如蒋南翔未从清华毕业;有人从理工类转为文史类。姚依林在回忆中就承认,“我原来是学化学的,搞运动,搞工作,书念不下去。我的普通化学,要经常做实验,我没有时间去做。结果张子高先生只给了我60分。这样,我只好转入历史系。”李昌从物理系转入历史系,燕京学生会主席朱南华从医预科转入历史系,原因之一也是学习跟不上。
“一二·一六”游行之后,清华学生内部分裂,左右两派斗争激烈。同学们对于抗日救国几乎无分歧,区别在于左派学生“反蒋”抗日,右派学生“拥蒋”抗日。还有一部分中间学生只想念书,支持抗日,不涉党派,未必欢迎革命。星星之火,不能燎原,对某些左派学生领袖而言,中、右派的立场都难以接受。
清华的左派学生人多,可以在大礼堂开全校学生大会,称为“大礼堂派”或“救国会派”;右派学生人少,只能在同方部开会,称为“小礼堂派”或“同方部派”。同方部当时用于清华小型聚会,也作为学生下棋等娱乐活动、演戏舞台。曾命名为“九一八纪念堂”,并有横额悬于门楣之上,数年后迫于日寇的压力,横额被摘下。
居浩然说:“(清华学生)主流是救国会派,控制学生代表会干事会,对外代表全体。反主流是同方部派,人数号称三百,实只百余,对外限于个人活动。”何炳棣说“同方派”,“原是毫无组织经验的乌合之众。内中虽有国民党同学六七人,除一人是江苏籍外,其余都是东北逃亡入关,历经千辛万苦考进清华的,平时不得不用功,也不得不遵守清华良好的政治传统的。”
1936年12月25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获释。学生中的左右纷争没有平息,反而进一步激化。圣诞之夜,左派学生泄气,右派学生张扬,终于爆发何炳棣所称的“清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群殴”。
事件导火索是当晚9时左右,何炳棣带领同学自行搜查救国会办公场所,留下一片狼籍,果然搜出“危害国民政府”的确凿文献证据──“张学良和杨虎城津贴民族解放先锋队400元的收据”!他又“强迫工友开高班同学何凤元(注:清华地下党前支部书记,时任中共北平临委委员)的房门,搜查秘密文件而一无所获”。
左派学生闻讯赶来围攻,左右双方群殴开始。始作俑者何炳棣不吃眼前亏,走为上计,自称“杀开一条血路,急急跑向北院刘崇鋐先生(注:时任清华历史系主任)寓所‘避难’”,午夜“才一人溜回七院宿舍”。
次日上午,何炳棣去梅贻琦校长寓所交查获的400元收据。出门即遭左派学生围堵,他摆脱后沿路又遇左派学生追打。数学系杨武之(注:杨振宁之父)教授散步至此,劝阻说:“同学不可以打人。”见到梅贻琦后,声称极愿将收据交校长,“可是有一条件……”。话未说完,被梅贻琦打断:“学生不能向校长提条件。”
他马上道歉,并改口为“提出请求”,有三条:一、“请校长下命令所有左右两派组织全都解散”(注:实际上是凭400元收据,解散左派组织严密的救国会);二、“这件机密的收据由校长毁掉”;三、“清华的事由清华内部解决,不要再向外宣扬惹出是非”。梅贻琦答复,他个人的想法和何炳棣的请求“相当接近”。
65年后,何炳棣在《读史阅世六十年》中描述此事来龙去脉,口气坦荡自豪,“我对1936年底的政治斗争至今没有遗憾,正是因为我从未丧失过‘清华人’最低必要的道德与尊严。”确实,他不曾拿收据向国民政府告密,亦未危害不同政见的同学,底线应该点赞。
梅贻琦治校平衡有度,对左、右两派学生各打五十大板。擅自搜查救国会和学生宿舍、挑起群殴的一批右派学生记过,其中何炳棣“领衔”,因违反校规被记两大过;左派掌控的“救国委员会”予以解散。
此事还有一个“左右攻防”的花絮。12月26日,清华救国会发布《关于救国会被劫存件敬告教授及全体同学书》,指责右派学生“至彼无耻的侮蔑,谓搜得‘张学良之捐款收据’案,这更属笑话。”12月28日,《清华副刊》发表《救国会委员黄绍湘述二十五日学生会被捣毁的经过》一文,声称“要搜反动证据自然决不会有,但是这些人既然像暴徒似的在这儿抢劫,难道不会带些反动东西来诬赖吗?”
何炳棣从1991年出版的《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上看到这两篇文献后,发挥自己历史考证的专长,辨析质疑两文的逻辑、措辞、史实,甚至成文时间,如前文“肯定不是事件后一日(12月26日)撰就”。而且他又引蒋南翔《纪念一二·九早期战友何凤元同志》一文(《清华校友通讯丛书》,1988年4月),佐证自己搜查出的这张收据不是空穴来风。
蒋南翔在该文回忆:“1936年10月,中共北平学委成立后,曾派何凤元同志与北平学联主席黄诚等几位同志代表北平学联到西安张学良东北军做联络工作。事毕以后,他没有同黄诚同志一起回北平,而是由组织决定留在西安《西安民报》当编辑。”
(2017年8月8日01:10,【山水微言·163】。本文为“师表校魂”大学校长系列之六, “蒋南翔史评三重奏”之青运篇 ,连载第7节,2018年12月7日在FT中文网部分发表。)